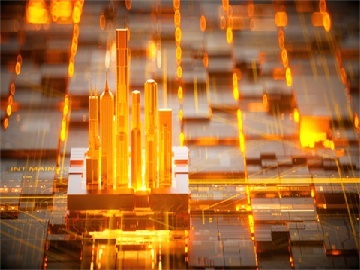河北资产港股IPO:AMC的第一枪,不会是个哑炮吧?
 摘要:
河北资产冲击港股IPO,背后是一场关于地方AMC能否“讲出新故事”的生死试验。2025年6月27日,河北资产管理公司向港...
摘要:
河北资产冲击港股IPO,背后是一场关于地方AMC能否“讲出新故事”的生死试验。2025年6月27日,河北资产管理公司向港... 河北资产冲击港股IPO,背后是一场关于地方AMC能否“讲出新故事”的生死试验。
2025年6月27日,河北资产管理公司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并首次披露招股书,若成功,将成为首家赴港上市的地方AMC。
对于地方AMC说,上市之路可以说异常艰难,如今在香港上市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只有中国信达和中信金融资产(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),为四大国资AMC巨头之二,地方AMC尚无成功上市先例。
不是最大的一家,也不是最赚钱的一家——这家总部位于石家庄的资产管理公司,总资产不过75亿元,2024年利润回暖至2亿元,但几乎全靠一笔地产处置收益撑起;头部客户占比近五成,结构极度集中。
看起来,它不是最合适的那个,但偏偏走在最前面。这一步,既显得仓促,也显得迫切。
河北资产此时谋求IPO,公司从完成股改到递交申请仅间隔10天。与其说是抢跑资本市场,不如说是地方AMC试图在融资、监管与市场估值三重压力下,提前“突围”一次。它借助存量项目释放利润,压着周期交出一份漂亮报表。
过去二十年地方AMC依赖政策、资源与非标路径存活,如今监管收口、估值体系重构,它们还能留在牌桌上吗?河北资产,只是第一个把赌注压在资本市场的。
河北资产的样本意义:小体量公司里的行业镜像
若不是递交了招股书,河北资产这家设在石家庄、牌照背景并不突出的地方AMC,很少被市场注意。全国持牌地方AMC已有近60家,它的资产规模与业务体量都谈不上突出。但其财务结构与盈利模式,却映射出整个地方AMC行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常见处境。
成立于2015年的河北资产,实际控制人为河北省国资委,是河北省唯一具备批量收购及处置金融不良资产资质的地方AMC。从市场份额来看,其在河北省的不良资产收购领域中排名第二,占比达24.4%;而在中小银行处置领域则位居第一,占比高达47.2%。在区域内,它的地位等同于“准官方收债人”。
截至2024年底,河北资产总资产为75.56亿元,其中超过40%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;负债50.39亿元,资产负债率为66.69%。公司的盈利很大程度依赖不良资产的回收节奏。2024年录得2.04亿元净利润,并非新业务大规模展开,而是原有资产组合进入处置期所致。
河北资产的盈利波动,几乎可以作为地方AMC普遍面临的不确定性缩影。2022年公司盈利不足1亿元,2023年因项目回款断档、公允价值变动带来账面亏损,全年亏损1.45亿元;而2024年则靠4.4亿元的估值收益大幅反弹。这样的盈利模式,很难建立持续性。
更大的风险隐藏在客户结构中。2014年,河北资产公司超过66%的不良资产经营收入来自前五大客户,而仅石家庄一家房地产公司就贡献了近五成营收。这类结构性集中,意味着当某一客户偿付节奏改变时,整个利润表就会失衡。招股书显示,这家客户2023年几乎未形成实质性回款,成为当年亏损的关键因素。
与此同时,公司营收的构成也透露出对估值模型的高度依赖。2024年收入大幅增长,很大一部分是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账面调整所致,而非实际回款。也就是说,这种利润并不具备强现金流支撑,一旦未来实际清收与估值脱节,利润就有被回吐的可能。
财务结构上,公司仍高度依赖外部融资。截至2024年底,其银行贷款余额为19.33亿元,占全部负债的近四成,而净资产仅为25亿元,杠杆水平并不轻。
一旦上市成功,河北资产将面临从准政策机构向市场化主体的跃迁,而支撑它当前利润的结构,在公开市场的审视下是否站得住脚,是否具备对冲“周期性空窗”的能力?目前仍未可知。尤其在不动产领域持续处于回收困难状态的今天,靠几笔集中回款拉起收入天花板,远不足以让资本市场长期买单。
上市的窗口可能只有一次,河北资产这一跃是腾空还是探底,未来两年将见分晓。
河北资产并非个例。大多数地方AMC在设立初期依托地方财政资源和平台项目运作,形成了较为粗放的纾困和回收体系。但随着监管收紧、融资趋紧,这套路径已难为继。本次冲击上市,更像是在传统盈利模式被迫终止之后的一次被动突围。
监管紧箍收紧,地方AMC转型的时间正在被压缩
河北资产选择在2025年初申报上市,不只是出于自身的节奏,也是对整个行业监管形势的一次被动应对。就在过去一年,地方AMC赖以生存的若干关键路径——跨省展业、结构化分销、平台融资协作——正逐步被一道道红线划清。
监管部门对地方AMC的新一轮整顿,早在2024年初已现端倪。年中,一份《地方AMC监督管理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在业内流传开来,内容虽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,但多地金融办已按其精神执行先行调整。最直接的变化,是限制区域经营,不再允许省内AMC通过“合作机构”将个贷包向外省转让,部分主营零售不良业务的机构因此营收骤减;更深一层的,是要求所有交易回归表内,不得再通过保底协议、回购安排实现“非公允价格”处置。
以往那种靠结构设计获得短期账面利润、再用估值调节推动资本动作的逻辑,正在被整体否定。原先属于“灰色地带”的业务模式如今正逐一被清理,行业必须重建在合规与真实利润之上的商业模式。
这种变化带来的压力不只在监管侧,也体现在准入门槛和成本结构上。比如“不得倒包催收”这一条新规,导致AMC不得不自建清收队伍,成本上升三成以上。对于原本依赖外包轻资产运营的AMC而言,这无异于换了另一套运营逻辑。
这意味着,“拿到牌照”不再是“能赚钱”的保证,而是“必须自建体系、自担风险”的沉重义务。一些地方AMC虽然持牌,但无能力满足合规要求,也无力构建催收与风控体系,最终被迫混改、转让、甚至直接退场。
一整套政策调整正在改写AMC行业的底层叙事。一些省份的AMC则在尝试引战混改,但进度普遍缓慢,背后是市场对其资产结构、持续经营能力的不信任。
河北资产此时推开港交所的大门,其实是被政策倒逼下的一种前置动作。一边是本地不良资产规模在压缩、回收周期拉长,另一边是传统融资渠道趋于收窄。当监管信号日趋明确,河北资产已难以等到地方AMC改革的整体节奏,只能率先将自身“推向市场”,搏一个估值,也搏一条出路。
命运重估:AMC价值的最后一轮重定价
2024年末,黑龙江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悄然从地方AMC名单中退出,没有发公告,也没有太多媒体关注,只在监管公示中留下一个模糊的“业务整合”注脚。此前几年,类似的动静接连发生:山东、吉林、辽宁等地的AMC开始“混改”或“引战”,一些公司挂牌股权转让,底价一降再降,却鲜有真正接盘者。根据公开信息,截至2024年,全国59家地方AMC中,已有12家启动了股权变更或混合所有制改革。
地方AMC到底还有多少价值,这成为市场难以回避的问题。
曾几何时,这张牌照本身就是资源。2000年代初四大AMC成立之际,每家背靠国有银行的坏账包袱,是时代赋予的原始资产;到了2014年,地方AMC陆续获批,成为地方政府盘活资产的重要平台。彼时经济仍有扩张空间,不良资产交易活跃,AMC靠着打折买入、催收变现、司法处置,可以在灰色地带中获取可观利润。更重要的是,它是地方政府面对庞大隐性债务时,最方便使用的“出表工具”。
但如今,这种套利通道正在坍塌。
2023年底开始,监管对AMC的监管框架发生明显转变。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明确提出地方AMC“不得跨省经营”,并列出“不得开展五类业务”,其中就包括与实际控制人、地方平台之间的非公允交易。这意味着,AMC与地方城投之间以往相互做局、相互腾挪的路径基本被堵死。
不仅如此,地方AMC还面临一项硬约束:金融不良资产收购比例不得低于30%。但2023年,全国仅有12家AMC达标,其余公司仍主要依靠对地方平台债、城投类项目的资产重组维持业务。而个贷催收业务也遭遇监管收紧,2023年起禁止个人不良债权的二次转让,许多AMC被迫自建催收团队,成本上涨30%-50%。
从盈利能力看,地方AMC普遍下滑。河北资产2023年账面亏损1.45亿元,已属其中佼佼者;更多未上市机构的年报披露显示,不良资产经营收入增速下滑,资产减值准备飙升。一些机构甚至不得不依赖关联公司“做收入”或“反向注资”来维持报表平衡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部分地方AMC走上了自我变现的路:主动将牌照资产推向市场,寻找更强的资金方来接盘,或以控股权置换增资扩股。而河北资产选择的是另一条更激进的路——登陆港股,用二级市场的估值,重新给自身定价。
这既是自救,也是一次整体价值的再评估。倘若河北资产的IPO最终得以推进,并获得理想估值,不排除会成为一批省级AMC转向资本市场的先例;反之,则可能验证AMC牌照红利期结束的市场共识。
监管的态度,将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从目前来看,无论是中央汇金控股长城资产、信达资产,还是对地方AMC的限制新规,逻辑都指向一件事:AMC已从“政策通道”转变为需要接受市场约束的普通金融机构。其估值,不再依靠牌照与特殊关系的溢价,而回归到可验证的资产质量、业务模式与盈利能力之上。
在这样的趋势下,AMC的“最后一轮重估”或许已经开启。至于估下来的是泡沫,还是价值,就看这一轮是否真的有人愿意买单。
地方AMC的资本化探索:不止IPO一条路
河北资产冲击港股IPO,并不是孤立事件,它只是地方AMC在融资窗口收紧、监管高压持续的背景下,所选择的诸多资本化路径中的一种。事实上,在河北资产敲开港交所大门的同时,其他AMC正在同步上演一场静悄悄的结构重构。
在国家级AMC层面,中央汇金于2025年4月对长城资产实施了一次高规格的“外科手术”:通过“减资+增资”组合拳注资368亿元。此举旨在挽救这家因连续巨亏(2022年亏损453亿元)濒临资不抵债的机构。操作完成后,汇金持股比例跃升至93.34%,彻底清洗原战投股东,长城资产净资产得以恢复至579亿元,资产负债率从96%降至90%。这场由国家队主导的“体外抢救”,是国家对系统重要性AMC风险的精准干预。
视线转向地方,重庆选择了另一条整合之路。地方政府将水务资产、城投平台以及AMC、信托等金融牌照子公司股权集中整合,打造城市金控平台。这种以城投信用为基石、打包金融资源的模式,本质是对分散的城市信用与金融资产进行系统性重估与资本转化,寻求整体协同效应。
头部机构信达资产则展现了不同的策略。它通过投资并转股浦发银行可转债,成为银行股东,实现了AMC与银行体系间的深度资本协同。这一路径虽未直接改善自身不良资产质量,却通过绑定银行体系更低的融资成本和稳定渠道,为处置业务开辟了间接支持空间,可视为一种“牌照互换”式的资源协同。
尽管路径各异——河北资产试图借IPO换取市场信用,长城资产依赖国家注资重塑资产负债表,重庆通过城市资源捆绑构建新平台,信达则寻求与银行体系的横向协同——其核心目标却高度一致:在监管套利空间消失、传统财政暗补难以为继的严苛环境下,盘活资产、补充资本、稳住控股权。这场资本路径的分化,正是对过去十年地方AMC依赖“定向处置+城投担保”模式的集中回应。当监管强行收口、财政无力兜底,寻求更具市场化和可持续性的资本支持机制便成自然而然的出路。
河北资产只是率先站上资本聚光灯的探路者。可以预见,“长城式”的股东再造、“重庆式”的资源整合、乃至更多未浮出水面的“信达式”协同,将在监管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加速涌现。只是这些转型,不会写进招股书,却将深刻改变整个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资本叙事。
结语
河北资产能否顺利完成港股上市,现在还无法定论。它选择在监管趋严、业务承压的当口走向公开市场,无疑是在赌一个窗口期——既赌估值体系尚未完全重构,也赌资本市场还愿意给AMC这类机构一些时间。
正如财新所讲的那样,AMC制度日益沦为“四不像”:不像资产管理公司、也不像金融控股公司,不具备典型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,更没有作为国有资产平台应有的公共责任约束。它们从来不是为了赚钱而设立,却又不断以商业化扩张和监管套利作为生存路径。
河北资产这次脱离“四不像”困境的尝试能走多远,关键仍在三件事:第一,监管是否最终明确AMC在市场体系中的角色边界;第二,市场是否愿意给“以不良资产起家的公司”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估值锚;第三,地方政府是否还愿意继续在AMC身上押注,把它作为资产重组和债务缓释的外部化工具。
2025年,AMC这类机构正经历其20多年生命周期中最深的一次结构调整。旧逻辑退场,新模式未立。像河北资产这样试图“自证价值”的动作,或许会越来越多。
但不确定性也在放大:不良资产能否顺利处置?项目来源是否合规?估值基础是否牢靠?二级市场是否买账?这些问题,没有一项可以绕过。能否成为地方AMC的新模板,还需资本市场与监管层共同给出答案。